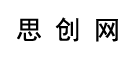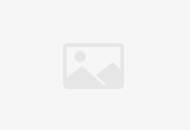呼啸山庄和简爱那个更让你心动为什么?
如果把简爱同凯瑟琳做一个比较的话,可以生动的说,是公主与灰姑娘的比较。你不可以说谁比谁更美丽,公主并不是因为有了珠宝的装扮而显得华美,灰姑娘也不会因为暗淡的颜色而失去美丽的光环。美丽,是她们共有的资本。也许是生存条件的差别,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她的生活遭遇令人同情,但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平等幸福的精神更为人们所赞赏。她爱的深,爱的真,不会因为他的穷困潦倒而离开,也不会因为他的富有而留下,她的爱不允许有一粒沙子,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坚持什么和应该坚持什么。而凯瑟琳,含着金汤匙的公主,我们不可以否认她是善良的。但是舒适的生活,使她失去了独立的资本,也使得这成为了她放弃真爱的借口。是的,你可以说她自私,说她虚荣,她就是为了钱,为了埃德加向的漂亮而答应求婚的。但是,你可以那样堂而皇之的指责她么?不,你不可能奢求温室中的花朵会向往风霜雨雪。即使向往,那也仅仅是向往罢了。她没有勇气面对那样的生活,即使真爱,她也做不到。你可以说她不爱么?“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最强的思念。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了,而他却毁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那这段感人的深情告白又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只能说她不敢,她,不能!简爱和凯瑟琳注定是不一样的人,也注定她们有着不一样的结局。虚荣的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虚荣埋单,而勇敢真诚的人,勇敢也注定会对她负责。第二章 罗彻斯特VS希刺克厉夫小说中描写罗彻斯特,他其貌不扬,是个性格阴郁而又喜怒无常的人,虽然有着巨大的财富,但是有着失败的婚姻。你说他的命运是悲惨的,我不否认,从他的性格就可以看出。很少有生活幸福的人会阴郁而喜怒无常吧?但是,我也不支持,因为简爱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他精神为之一振。罗契斯特过去看惯了上层社会的冷酷虚伪,简·爱的纯朴、善良和独立的个性重新唤起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而他能真诚地在简面前表达他善良的愿望和改过的决心。一个人曾经的虚伪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虚伪。谁都有犯错误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强加指责,因为谁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是,简爱让他有了改变的决心,这是多么的难得啊!如果没有真正牵动心灵震撼心灵的爱,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痛定思痛的决心呢?而我们的另一个男主角,希刺克厉夫,他也变了,他从最开始的一个平凡的小卒,变成了一个巨富的富翁,从一个善良单纯的人,变成了满腹仇恨的人。他的改变,可以说是可怕的,甚至是血腥的。他的改变也是为了爱,因为他深爱的女人没有和他在一起,为了金钱背叛了自己,所以,他要变强,他要用自己的金钱折磨那些因为钱折磨过自己和背叛过自己的人。他真的变了,彻头彻尾的变了,变得我们觉得陌生了。但是,他的爱没有变,一丝一毫也没有变,我们可以想到,是什么支撑着他那样的拼命达到今天的成绩呢?就是他对凯瑟琳的爱,强烈的甚至有些畸形的爱。但是,我们不禁觉得可悲,改变,一定要变的让自己痛苦,让爱人心痛么?那么你改变的初衷是什么?你是不是偏离了最开始的航道了呢?爱让你们相遇,爱让你们改变,只是罗彻斯特在向着光明,希刺克厉夫在向着黑暗。我们没有权利去指责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们,而他们的改变,也注定了他们一喜一悲的结局。第三章 当简爱遇到呼啸山庄当姐妹俩的巨作同时问世时,《简爱》受到的欢迎程度是不可想象的,而《呼啸山庄》却是受到了那样的冷漠。无论人们如何的喜欢也好,如何的讨厌也罢,他们都是不可多得,震撼人心的美丽而又灵动的文字。《呼啸山庄》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而《简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驱使人拿起这本书,随之深深感动,心灵也为之震颤。当他们相遇的时候,我们无法辨别出谁比谁优秀,谁比谁出色,我们只能说,一个是温暖人心的左手,一个是震撼人心的右手,缺一不可。《简爱》和《呼啸山庄》都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美丽的女子和轰轰烈烈的爱。我不想用哪个倡导了女权的独立,哪个揭露了人性的悲哀来辨别他们,我觉得那是一种玷污。我看到的《简爱》和《呼啸山庄》就是两段刻骨铭心的爱,两段让我心动的爱,两段注定了结局的爱,两段流传千古,还会一直流传下去的爱……
《简爱》《呼啸山庄》哪个更真实?更有文学价值?更好看?
无论是文学上的创作技巧,还是作品的深度,《呼啸山庄》都更胜一筹呼啸山庄,希拉克里夫的“复仇”是一以贯之的,从始而终,这种主题19世纪文坛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其中更掺杂了感情的问题,这两者多少是有冲突的,这就构成了这本小说隐性而内敛的力量,藏在复仇和爱情的文字背后,让读者感到人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知,多么难以把握。一个场面当属希拉克里夫把小凯蒂抓到呼啸山庄,威逼她和林淳完婚的一幕,希拉克里夫癫狂了,他动粗打人,小姑娘也不放过,嘴里骂着脏话——那一刻是他复仇高潮来临前的一秒,是最紧张,最激烈的片段!那是人性冲突而矛盾的顶点,是人内心最深处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艾米丽毫不手软地展现给读者,几乎不带感情,这是这位19世纪的英国女作家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她冷静而残酷,她旁观而犀利。
自从夏洛蒂•勃朗特诞生以来,一百年过去了,她已经成为这么多传说、热爱和著述的中心,但是她自己只活了三十九岁。假如她能活到一般人那么大的岁数,这些传说又会有什么变化,想一想倒也怪有趣儿的。她也许会像同时代的某些名流那样,成为常在伦敦和别的什么地方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无数的图画和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部小说以至于回忆录的作者,但是跟我们难免有些疏远,只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年人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她也可能很富裕吧,也可能诸事顺遂吧。但事实还不是这样。我们一想到她,就得想象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命运不佳的人;就得让我们的头脑退回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退回到在约克郡勃朗特姐妹的家乡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哈渥斯小镇。的偏僻荒原上的那座牧师住宅。而她就一直待在那座住宅里、那片荒原上,既受过穷也受过捧,但是永远不幸,永远寂寞。
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想必也要在她的作品当中留下痕迹的吧?我们想:一位小说家,自然要靠着许多许多难以经久的材料来构筑他的作品,这些材料一开始虽能给他的作品增添真实性,到后来可就要变成累赘无用的东西了。当我们又一次打开了《简•爱》,心里禁不住犯疑:她用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会不会只是一个陈旧的、过时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世界,就像荒原上的那座牧师住宅,只有好事者才去参观、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呢?我们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打开《简•爱》的。可是,读了两页,一切疑虑都一扫而光了。
"起着皱褶的猩红色帐幔遮住我右方的视线;左边,明净的窗玻璃保护着我,却不能使我与那阴凄凄的十一月的白天隔离。一面翻动着书页,我不时抬起头来审视这冬日下午的景色:远处呈现出一派灰蒙蒙的雾霭;眼前是湿淋淋的草地和正被风吹雨打的灌木丛,而那绵绵不停的雨,在久久哀号的狂风吹送下,唰唰唰地飘向远方。"引自《简•爱》。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里的荒原更不能经久、比那“久久哀号的狂风”更容易受到气流的支配而变幻不定了。同样,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兴奋状态更为短暂易逝?但它竟然催着我们一口气把书读完,不容有时间思考,不容我们的眼光离开书页。我们被小说如此强烈地吸引,假如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那动作也好像是发生在约克郡,而不像是在你的房间里。作者拉住我们的手,迫使我们跟她一路同行,让我们看她所见到的一切;她一刻也不离开我们,不许我们把她忘记。最后,我们就完全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义愤之中了。与众不同的面孔,轮廓突出、相貌乖戾的人物,都在我们眼前闪现;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的。她一走开,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想到罗契斯特罗契斯特,《简•爱》中的男主人公。,我们同时也就想起简•爱。想到荒原,我们也不能不想起简•爱。甚至,再想一想书里的客厅,那些“好像覆盖着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只淡白色的巴洛斯壁炉面,壁炉上那“红宝玉一般鲜红的”波希米亚玻璃片,以及那“雪白与火红相间的混合色彩”---如果把简•爱撇开,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简•爱的缺点是不难寻找的。总是做家庭女教师,总是陷入情网——这在一个许多人既不当家庭女教师、又不爱什么人的世界里,毕竟是一个严重局限。与此相比,像奥斯丁或者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具有数不清的侧面。他们活得生气勃勃,对于许多不同的人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而这许多人就像镜子一样从多方面映照出他们的性格。他们随意在各处走动,不管作者是否在察看他们;在我们看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而这个世界一旦由他们形成,我们自己也可以进去见识一番。从个性的力量和眼界的窄狭来看,托马斯•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倒是互相接近的。但是,两个人的差别也很大。我们读《无名的裘德》,不会急急忙忙一口气看到结尾——我们往往掩卷沉思,生出一连串题外的念头,在小说人物的周围造成一种疑问和讽喻的气氛,那是他们自己浑然不知的。尽管他们不过是些纯朴的农民,我们却不得不向他们提出种种事关重大的难题和疑问;因此,在哈代的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仿佛就是那些无名的人。这种本领,这种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一点也没有的。她并不想去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她甚至根本就没有觉察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了这么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
因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积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他们的心灵所产生的一切无不带着他们自己的特征。他们很少从别的作家那里学习什么,即使采取一点儿什么,也消化不了。
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的风格似乎都是拿一种生硬而庄重的报章文体作基础而形成起来的。他们笔下的散文往往板滞而不灵活。但是,他们两位通过长期专注的努力,对于自己的每一构思都要凝神细思直至为它找出确切的语言,终于锻造出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散文——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
至少说,夏洛蒂•勃朗特有成就并不是靠着她读了很多书。她从来不会像职业作家写得那么顺溜,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博采词汇、运用自如。
“我无法满足于跟那些力量雄厚、心思细密、情趣高雅的人们互相交往,无论他们是男是女,”她如此写道,口气像是某外省报纸的社论作者;接着,她又恢复了自己那火辣辣、急切切的口吻,说,“除非我首先冲破了传统保留下来的外围工事,跨过了自信的门槛,并在他们心中的炉火旁边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她也恰恰就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地位;正是那内心之火的摇曳不定的红光照亮了她的书页。换句话说,我们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不是去找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都是既生气盎然而又性格单纯的;不是去找喜剧性的情节——她的情节是既严酷而又粗糙的;不是去找关于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个乡村牧师女儿的念头。
我们读她的书,只是为了其中的诗意。或许,一切像她这样个性特强的作家都是如此吧。正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常说的:他们只要把门打开,别人就能把他们的一切看个一清二楚。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跟既定的事态总是格格不入——这促使他们渴望立即投入创作而不肯耐心观察。这样的创作热情,抛开半调子,排除小障碍,飞越过那些常人琐事,一下子就抓住了作者自己也还说不大清楚的七情六欲。这使得他们成为诗人,即令他们想用散文写作,也不受任何约束。因此,艾米莉和夏洛蒂两人常常乞求大自然的帮助。
她们都感到需要借助于某种比人的语言行动更为强大的象征力量来表达出人性当中那许许多多还在沉睡的情感和欲望。夏洛蒂的最好一部小说《维列特》就是用了一段关于暴风雨的描写来收尾的:“天空低垂,阴霾密布——一大片散乱的飞云自西方飘来;云彩幻化成为种种奇形怪状。”这样,她请大自然把无法用其他方法表达的心情描写出来。但是,对于大自然,这姊妹俩哪一个也没有多萝西•华兹华斯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名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观察得那么准确,也没有丁尼生丁尼生(AlfredTennyson),英国诗人。描绘得那么细致。她们抓住的只是大地上某些跟她们亲身感受到或者转嫁在人物身上的东西非常近似的方面,因此,她们笔下的暴风雨、荒原、夏日的美好天气,都不是为了点缀一下枯燥的文字,或者显示作者的观察能力,而是用来贯通作者的情感,亮明书中的意图。
常常,一部书的意图既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在于说了什么话,又不在于作者自己从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当中看出了什么联系,这么一来,了解起来自然很难。特别当一位作家像勃朗特姊妹那样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意图和他的语言难解难分,而且只是一种情绪,并非什么细致的观感,要了解就更难了。
《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为难懂的书,因为艾米莉乃是一个比夏洛蒂更加伟大的诗人.夏洛蒂写作的时候,总是带着雄辩、光彩和激情说道:“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感受虽是非常强烈,却和我们的感受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里既没有“我”,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又没有雇主。那里面有的是爱,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
艾米莉的灵感来自某种更为广阔的构思。促使她创作的动力并不是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也不是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她放眼身外,但见世界四分五裂、陷入极大混乱,自觉有一种力量能在一部书里将它团在一起。这种雄心大志在整个小说里处处可以感觉出来——它是一场搏斗,虽然遭受挫折,仍然信心百倍,定要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一番道理,那不仅仅是“我爱”,“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但这句话并没有说完。情况如此,也不奇怪;令人惊奇的倒是她竟然能够使我们感觉出来她心里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在凯瑟琳•恩肖凯瑟琳•恩肖,《呼啸山庄》中的女主人公。那只说出一半的话里所透露的便是这种心情:“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只要他还存在,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还存在,而他却被毁灭了,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就变得完全陌生,我似乎也就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了。”这种心情当着死者面前又一次流露出来:“我看到了那种无论人间、地狱都不能打破的安息,我也感到了对于那无穷尽、无阴影的来世的确信——相信他们已进入了永生——在其中,生命无限长久,爱情无限和谐,欢乐无限圆满。”引自《呼啸山庄》。
由于这部书暗示出了在人性的种种表象下面所潜伏的力量能将它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这才使得它与其他小说相比具有自己的非凡高度。但是,对于艾米莉•勃朗特来说,仅仅写几首抒情诗,发出一声叫喊,表示一种信念,自然是不够的。因为,关于这件事,她在自己的诗歌里已经爽爽快快地做过了,而她的诗歌也许要比她的小说更能传诸久远。然而,她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她还得担负起一件吃力而又不讨好的任务。她必须正视别样的生存状态,与种种事物的表面结构打交道,要把农庄和房舍建造起来,像真的一样、让人一看便知,还要把在外界独立存在的男人女人的谈话记录下来。
因此,我们得以攀登上这些感情的顶峰,不是由于什么豪言狂语,而是因为听见了一个女孩儿坐在树枝间一面摇摇荡荡、一面唱出了几支古老的歌曲,看见了荒原上的羊群正在啃吃草皮,倾听着柔和的风正在草间低语。农庄上的生活,连同其中发生的种种荒诞无稽、叫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都一下子揭开了。
我们有了一切机会,可以将《呼啸山庄》与一座真正的农庄、将希刺克厉夫希刺克厉夫,《呼啸山庄》中的男主人公。与一个真实的人物加以比较。我们可以问一问:既然这些男男女女跟我们自己看见的人如此不同,那么,真实性、洞察力、或者说细微的感情色彩又在哪里呢?
可是,即使这样问了,我们仍然看到希刺克厉夫毕竟是一个只有天才的姊妹才能识别出来的兄弟;我们可以说他叫人讨厌极了,然而,在文学领域中又有哪一个少年人物能像他这样生气勃勃地活着?大小凯瑟琳指《呼啸山庄》中凯瑟琳•恩肖及其女儿凯茜。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任何女人都不会像她们那样感受、那样行动的。但她们仍然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女人。
作者似乎把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特征都撕个粉碎,然后再对这些无法辨认的碎片注入一阵强劲的生命之风,于是这些人物就飞越在现实之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她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
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什么关系
《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姐妹关系。《简·爱》的作者是夏洛蒂·勃朗特,19世纪英国女作家,是“勃朗特三姐妹”里年龄最大的,也就是大姐。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艾米莉·勃朗特,英国女作家、诗人,她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安妮·勃朗特之姊。
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什么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4月21日~1855年3月31日),英国女作家。她与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史上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她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当过教师和家庭教师。由于生活窘迫和卑微境遇,使她的作品主题往往是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孤独,艰辛和奋斗。
而艾米莉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姊妹三人于1846年出版了一本自费出版诗集,以艾米莉为主。她的诗的风格往往是直抒胸臆,感情浓烈;景物描写常常荒僻,寂寥。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评论艾米莉诗作中的“热情、深沉和大胆”是拜伦死后无人可比的,但她的小说《呼啸山庄》掩盖了她诗歌的光芒。
安妮·勃朗特,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及艾米莉·勃朗特之妹,代表作是《艾格妮丝·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府上的房客》。其中,《艾格妮丝·格雷》被爱尔兰著名诗人、评论家乔治·莫尔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
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什么关系
1、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姐妹关系。
2、《简·爱》的作者是夏洛蒂·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艾米莉·勃朗特,1847年,《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在英国先后出版。《简爱》和《呼啸山庄》这两部作品的出现,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轰动;而这两部不朽的名著竟出于名不见传的两姐妹之手,更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更多关于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什么关系,进入:https://www.abcgonglue.com/ask/2ac2a31616090788.html?zd查看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