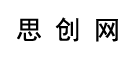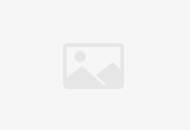流浪日记
1
大约在二十二三年前,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人生中第一次的流浪了。
那时候父母似乎刚刚在过去的新年后离了婚。他们不知道啥时候从镇子里回来,我是见过父亲或是母亲手机捏着的那本巴掌大的小册子的,封面似乎是绿色的,有些硬,上面印着三个竖排的大字:“离婚证”;里面用黑色钢笔写着姓名、籍贯云云,重点是里面有两栏写在印刷好的黑色分割细线里面的内容,我记得清楚:一栏是“孩子分配”的内容,另一栏是“财产分配”的内容。
“孩子分配”栏用黑色钢笔写着,长子随父亲生活,长女和次女随母亲生活;“财产分配”一栏则写着,因为洪水冲毁房屋,已无其它共有财产,也无其它共有财产分割。
其实在父母离婚前两三年,我早已经独自跟着爷爷生活了,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则一直在杭州务工。期间我的俩妹妹,据说时而呆在外婆家、时而呆在大姨家、时而又跟着母亲的新男友,跟着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地方,同样是深山老林的地方,上学。
说起流浪,俩妹妹似乎比我时间还早。时间已过二十多年,那时候她们还是孩童,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记得自己辗转奔波的生活,其实就是流浪。我想,最好早已忘却,因为想起来,流浪总是无奈与无力居多,你只能就着眼下的路走,有没有明天,明天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比如我,记住的流浪生活,其实真没什么美好可言,虽然很多旧事时隔二十多年,回想起来或许还有些回望的兴味,其实多的已是自嘲,但放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件美的事儿。
2
作为一个离了母亲的孩子,思念母亲的天性自然使他时常想念母亲。于我而言,何况还有十岁前成天可以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幸福经历。
离开母亲头两年,我在沉默与压抑中度过,所有的玩伴都不能在我面前谈论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会跟他们急眼。久而久之,玩伴们不再在我面前谈论有关母亲的任何问题,而实际上,我从年节时候村子里所有孩子们拉着自己母亲的充满热烈和欢喜的欢笑声中,更觉神伤。我常常徘徊在屋子的顶楼,默默地看着隔壁家孩子围在他母亲的周围而不自觉地泪眼婆娑。
再大些时候,我已有了强烈的寻找母亲的愿望。我的第一次流浪,就起始于那个空虚而又深深怀想母亲的暑假。
村子里本有不少玩伴,但是一到放暑假,玩伴们忽然一个个地不见了,我知道,他们都趁着放暑假,被父母接去外面的城市了。
一个夏日的午后,有人在屋外喊我,说隔壁家大爷找我,说他有我母亲的消息。我听到这个消息,原本寂静无物的内心,像一口沉睡了千年的活火山,忽然热烈而汹涌地迸发出万丈熔岩,滚烫而澎湃!我欢天喜地、急不可耐地飞奔出家门,直窜进隔壁人家。
隔壁大爷见了我,笑吟吟地告诉我,他刚从杭州回来,回来前,他见了我母亲,有我母亲的地址,还谈论了我的近况,还说我母亲让我去找她。
当我朝大爷要地址的时候,大爷却沉吟了很久,终于说:我都是骗你的,我没有你母亲的地址。最后他说,我能从你看我孙子的眼神中看出来,你想你妈妈。
如一盆烧得通红的木炭,忽遭一桶凉水的倾覆,原本热烈而满怀期待的内心,此刻只剩斯斯冒着余烟的挣扎。我颓废地走出大爷家,低着头,挣扎的内心却也埋下了一颗更为坚决的种子:找妈妈!
暑假已过一大半,那年八月,我从村长家接到母亲的电话,于是十分坚决地请求母亲,给我地址。母亲也怀着愧疚的语气说,我也想和别人一样,趁着你放假接你来身边玩,可是我怕你爸爸会寻着来,再则,我在外面打工过得并不好。最终,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把地址给了我。
中学上学放学的路上,集镇大路里头拐角有一堵墙,上面挂着一块牌子,黑色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着:豪华大巴,农历三五八去杭州。我也曾偶尔见着那辆去杭州的大巴车,它上半身白色,腰身以下灰褐色。从它身边骑自行车路过,总能见到里面一排排灰麻布颜色的靠头——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就常常想象着,自己能坐在里面,奔向杭州、奔向妈妈的怀抱。
不久,妈妈托村里人给我带来五十元路费,让我自己到镇子上坐车前往杭州,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其实也算是流浪。
车子傍晚出发,到达杭州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了。我下了车,口袋除去大巴车费二十五块,还剩二十五。我心想,打个出租车总够了吧,从江西乡下跑到杭州,这么远都才花了二十五,这剩下二十五,在杭州城里铁定是够的。于是我招手拦下一部出租车,掏出我藏了许久的小纸条——上面有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地址。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起初他没说话,看了眼我手心里纸条上的地址,便发动车子出发,顺手还掰下了前挡玻璃下的计费器,初始价格:11元。
坐在车里,原以为二十五元车费足够,随着前方计费器数字的跳动而愈加紧张起来——眼见着那数字一点一点地朝“25”逼近,我的心便随着汽车的轻微颤动而颤动起来。“糟了,一会到达目的地不够钱怎么办?”我心里开始一遍一遍琢磨起这个问题来。
我相信,自己时常盯着计费器的眼神以及因为极度不安而不自然的神态甚至坐姿,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
“小伙子,一个人出来找人呐?”司机开始跟我搭话。
“嗯,我找妈妈。”我嗫嚅着回答。
不久,车到目的地,这是一处街道路口。出租车计费器上的数字,显然已经超出了我口袋里的余额。
“找你妈妈补吧。”司机体谅地跟我说。
我下车,朝街道四周张望,再对照手上的纸条找门牌号码。对面马路一侧有一间门口亮着灯、摆着几张桌球台的店铺还开着门。我走近前,在铺面墙壁上,看到了我要寻找的门牌号码。没错,就是这!可是,妈妈在哪?
正当我站在这间亮着灯的店铺前不知所措的时候,停在道旁的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走了过来,他朝我伸手:
“你的纸条给我,我帮你问问。”
司机走进店铺,不一会,里面有个染着红色短头发的女主人从收银台出来。她看了看我的那张小纸条,再看了看我,说:
“没错,地址和电话都是我这。不过,我不认识他。”
“应该是哪位住在附近的客人留的。”染着红头发的女主人分析说。
出租车司机走到我面前,将纸条交还给我:
“小伙子,看来你还得在这等你妈妈。我得先走了,车费就算了。”
说完,司机重新坐进他的汽车,“嗒”地一声点火声,那辆绿色的出租车亮起红色的尾灯,拐个弯,消失在前面的路口。
我拎着随身带的一个小背包,里面塞了两套夏天的换洗衣裳,我紧紧捏着背包带,蹲在染着红头发女店主门口的桌球台边,心里想,啥时候才能等到妈妈出现呢?
又过了一阵子,染着红头发的女店主抱着一块毯子出来,她将大门前一张桌球台台面收拾了一下,把毯子铺上,指了指对我说:
“晚上先在这呆一晚吧,看明天你妈会来不。我要关门了,放心,外面的灯我给你开着。”
我没说话,只是满怀感激地看着她从角落拿出一根长长的头上带着弓形的铁棍,朝头顶的卷闸门一拉,门便“框框框”地下来了。女主人弯腰钻进铺里。
这一夜,染着红头发的女店主果然没有关掉门口桌球台上的灯。这盏在我头顶亮了一整夜的白灯管,成了那夜我所有恐惧和无措的唯一安慰——张开眼,世界还亮着,真好!
3
距离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大约一年半以后,在一个集镇赶集日,我又因为和爷爷闹别扭,从而偷偷抓了爷爷养的两只大肥鹅,挑到集镇上卖了,似乎同样换了五十多元钱,当天傍晚,我又坐上了从镇子前往杭州的大巴车。
这次,满以为轻车熟路,可以顺利找到妈妈了,可惜,我错了。
这次和上次一样,也是半夜到,但是这回我有经验了,提前预留了足够的出租车费到妈妈住处。下了车,来到妈妈曾经的住处,我傻眼了,妈妈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对了,由于是跟爷爷闹别扭偷偷出来的,事前我也没有跟妈妈说要去找她。
我徘徊在小巷子里不知所措。最后,我重新走上亮着路灯的街道,在一处公交站台的长椅上找到了安歇处。同样在背包里掏出我的衣服,就这么盖在身上,迷迷糊糊地躺了一夜。
天亮以后,我睁开眼看了看天上的太阳。时值初冬,夜里在长椅上并睡不安稳,此刻明晃晃的太阳显得既温暖又和煦。我擦了擦眼睛,收拾起衣裳,心有不甘地重新走进了妈妈曾经住过的那条小巷,心想,总不是昨夜夜色太浓,我找错地方了吧?
其实我知道自己没有找错地方,这时候再走进巷子,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不知所措。
妈妈确实搬走了,不住在这里了。我在巷子里来回晃荡了两圈,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在左思右想、漫无目的地转圈的时候,一位老阿婆喊住了我:
“小伙子,你找人?我看你转来转去好几次了。”
于是我告诉阿婆,我来找妈妈的,但是妈妈没住在这了。
阿婆朝我招了招手,喊我等她一下。阿婆进了屋,不一会儿,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五块钱的纸币:
“拿去买点东西吃。”
我默默接过阿婆塞给我的钱,心里既惊讶又感激,可是嘴里却没学会说谢谢,我只是低着头转身便朝巷子口走去。
我身上确实没钱了。家里偷了爷爷的肥鹅换来的钱,除了车费和出租车费,剩下一些早花完了。
在巷子外,我见到一家福建混沌店。花了三块钱,吃了碗热气腾腾的混沌。下面去哪呢?
我想起来,去年曾经跟妈妈去过叔叔那,叔叔在一个叫“半山镇”的地方开着一家五金店,路,我似乎还记得怎么走。
去叔叔那吧。于是,我按着自己记忆里的路线,向西北方向走去。“祥符路”,没错,就是这条路,一直跟着走,就能走到半山镇。我终于在某块路牌上,看到了前方道路的名字,而这条祥符路,就是通往叔叔那的一条大道。
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半山镇。我已经能看到叔叔开的店铺大门了!可是,我却不敢直接进去,为什么?不知道,对于自己这趟毫无理由的出行,我似乎也不知道怎么跟叔叔解释。
我在镇子外一条小河边徜徉了很久很久。最终,耐不住肚子的饥饿,我终于丢掉了自己的羞愧和不知名的自尊,背着我的小背包,走进了叔叔的店铺——今晚,我可不想再在公交站台的长椅上过夜了。
4
初三辍学那年,我再一次独自一个人跑去了杭州。这次,没有上一回的羞愧和自尊,因为我到了杭州,妈妈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说,没钱上学了,早点出来打工挣钱也是可以的,还给我举例隔壁家某某,初中毕业后出来挣钱,如今家里新房子做起来了,老婆也有了——按妈妈的意思,我也可以从此出来好好挣钱,然后回老家修房子、讨老婆、生孩子。不过也是,那时候能上高中的人并不多,更别提上大学了。
那时候,妈妈正在京杭大运河某个岸边的大菜市场里摆摊卖菜,我成了妈妈的助手。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然后踩着三轮车,骑过半个杭州城,到某个不夜城似的大型批发市场进各种蔬菜;回来以后,正好是早晨七八点。把摊位一字排开,早上上班之前的工薪族首先会来光顾菜摊子,九点以后,很多赋闲在家的老大爷老大妈们便来了;中午是最冷清的时候,傍晚下班后,菜市场还有最后一场喧嚣——夜色暗下来了,匆匆吃完晚饭,得赶紧上床睡觉,因为六七个小时以后,又是新一天的凌晨三四点,我和妈妈又该骑上三轮车出发了。
卖菜的日子似乎没过太久,年便悄悄地来到了我们面前。那一年,我跟着妈妈回了许多年未曾回过的外婆家。春节后,妈妈和舅舅阿姨们商议:要不,年后你们把他带到广州去做事?就这样,大年初四,我和舅舅、舅妈以及小姨一道,背着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出门的时候,天下着小雨,我记得外婆说:下雨好,雨是财,这回你们出去要寻到财了。
到了广州,这里没有雨,暖洋洋的大太阳天天顶在我们头上,从家里穿来的厚棉袄穿不住了,大冬天的居然只需要穿一件薄薄的长袖。
我跟着小姨去过几家工厂,无一例外,我们都只能站在工厂的大门外,眼巴巴地询问看大门的保安大叔:工厂还招工吗?——上世纪90年代末,能进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就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当时的电视新闻里看见过记者的采访:小伙子,你来广州几年了?干的什么工作?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坐在公交车上的年轻人,满脸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回答说,“来广州好几年了,在一家某某工厂做工,每个月能拿一千块钱”!一千块,我的天,那时候一斤猪肉只需要两块三,一个学校的高级职称教师,比如我的数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七百块,而我的班主任,他才拿四百块一个月。
我多想也能顺利进工厂务工啊!可惜,我和小姨跑了许多家工厂,最终没有一家工厂收留我们。
一个天边同样悬着一轮红日的傍晚,舅舅、舅妈、小姨,还有我,我们各自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垂头丧气地走在偌大的不知名的广州街头上。那天晚上,我们寻见一处没人住的似乎废弃许久的一长排一层矮房子,外墙上红圈刷着大大的“拆”字,而矮房子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有几间甚至还有床铺。当晚,我们为了省钱,大家将就着就在这排矮房子里住了一夜。
再后来,舅舅、舅妈似乎一起跟着熟识的同村人去做起了装修工,而我和小姨,则决定回家——我其实也没回家,火车把我们从广州拉到南昌,小姨径直坐汽车回外婆家去了,而我又踏上了东去的火车,准备投奔在杭州开五金店的叔叔,这事,还是妈妈找叔叔商量后定下来的。
与小姨分别后,我独自一人坐在绿皮火车上,心里想起前不久出门时天上下的小雨,还有外婆跟我们说过的话:这回你们出去要寻到财了。想了想,心里不觉苦笑起来,财,在哪呢?
后来在杭州跟着叔叔做水电,我似乎又不是做这个的料,暑假里,我便被叔叔送回了爷爷家,准备继续新一学年的初三年级的复习。
5
高三那年,因为交不起高考报名费,我再一次选择了流浪。
大学毕业后,因为投奔同学,我还在厦门流浪过;接着又去了广东清远某一个小山村,跟着当地人搞起了养殖……
着实,我流浪的生活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当下,我已流浪到了四川攀西地区。
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我不知道。我这已过去的半生,几乎都在流浪中度过,少不更事时,我其实就已经跟着父母,经常坐着火车来回于父辈们奔波的路上,那时候,我只记得火车车轮碾压车轨的声音——哐当——哐当——
现在,“哐当哐当”的声音,又一次在我耳际响起。是了,我早已经奔波流浪于自己的路上,尽头,我还看不见尽头。
流浪日记
2022年3月9日,早上5点,从昨夜酒醉醒来。每次醉酒后醒来,干的第一件事:回想自己昨晚干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最讨厌第二天有人帮自己回忆自己醉酒后干的那些尬事。所幸,昨晚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从酒吧回来时,朋友和客户还在喝,我因为情绪低落和酒量有限,就先撤了。提着行李包,走在古城,晚上11点,古城里人也没几个,平常看来是有几分恐怖,可一个醉汉却没有那么多顾虑。回到酒店,像往常喝醉酒一样,想打电话找个人聊天,翻开通讯录,无人可打,或者“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便倒头就睡。
还有两个月,我就29岁了,明面上有车有房,却是一堆负债,本想去年年终发个8万可以把债还清,没想到因为销量任务没完成,被公司克扣了,导致现在还欠7万的外债和每个月的车贷房贷7000+。前段时间,刚和女朋友分手,情绪低落,感冒一个月咳嗽到现在也是没有好完。这一些列的事情,也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心,所造成的吧,可是我还想再看看我能有多窘迫。很多事情,慢慢的就理顺了,就算没有理顺,那也就习惯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在自我反省,做错了太多事情,才会面临今天这样的困境,也许真正的困境还在后面,那又怎么样呢?面对生活吧,没有那么糟糕。
这是我干业务第六年,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也没有逆袭,算是个不上不下的业务经理。可是,也会深夜叹息,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成功,为什么不长进,背井离乡出来,付出那么多心血,难道就是为了出来吃喝玩乐吗?不应该是这样的。该守住初心,好好干,该想想自己以后怎么走了。目前看来,规规矩矩上班,很可能还不清债务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利用自己的资源再拼搏一番。每个人都会面临那些风风雨雨,都会过去,多去经历,也是好的,但别迷失。
明天可能不会更好,但我有了面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