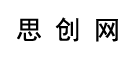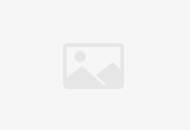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三月十五日晚上的十点二十,外婆走了,我没能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但我想,依着她的性子,是断然不希望我看到她弥留之际或许孱弱的样子。
几年前,惹了帕金森症的外婆来我家吃饭,午饭后我妈让我把外婆送回家。颤巍着拄着拐杖的她,出了家门不远就一个劲地念叨,让我回去:「这么大个人了,难道我还不认识回家的路?你是担心我丢了么?」拗不过她,我只好假意答应,嘱咐了句便转身就走,耳后传来的是「你走吧」三字,丝毫不拖泥带水。
我远远地跟着,原本十几分钟的脚程,她走了快四十分钟。远远见到她扶墙准备上楼时,只能感叹这老太太真是要强。因此我相信,外婆的最后一面是见过了,用她最后的骄傲和坚强。
今年春节,相比以往踩着除夕到家,这是我回家最早的一次。我也相比以往更早地去看外婆。外婆躺在床上,被妈妈轻微摇醒,说:「你看谁来了。」她睁眼愣了愣神,看着我对她笑,她也艰难地对我笑了笑。这是很多年来的默契,不论何时去见外婆,我总是不叫她,而是突然走到她面前,静静地站着笑着看着她,而她总会放下一切,笑着看着我,伴上一句:「就知道笑」。尔后就是她忙碌起来,翻箱倒柜给我端来几乎所有的零食。不论以前是每天去见她还是后来许久才见一次她,总是如此,就算是我长大几乎不怎么吃零食的时候,她也照例忙碌。
那两个小时,外婆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回来的,剩下的时间就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看着我跟妈妈说话,看着我不说话,看着我看着她。临走,我最后一个走出房间,转身问她,外面冷、有风,要不要把门关上。她只是略微仰头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似乎在那一瞬间我猜到了她的心思,这是我们祖孙俩最后的对望。
我总是要走的,就如现在外婆走了。几分钟后,我徐徐关上房门,在房门阻断视线的瞬间,她依然是那个姿势。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但不敢去想。外婆走的前夜,爸爸拨电话给我说:「外婆可能不行了。」当晚,我梦到了她,全是小时候的景象,而她要我带她去吃好吃的。
小时候,外婆总是会带我去吃好吃的。会在暑假,带我走很远,去附近的面条厂看挂面是如何做出来的。会带着我去买菜,看到新上市的干果总会问店家要一把,塞在我的口袋里。会看到我馋柿饼的时候,找到推着三轮车的小贩,买上一大袋之前,挑出一个个头最大的柿饼,拍一拍,抖落多余的糖霜,摘掉已经干得发硬的果蒂,再轻轻揉下,揉到她觉得足够软的时候才塞到我嘴里。所以,我印象里外婆的身影,总是高高的,挡在我身前,留下一堆美味的背影。也正是她,让我从小能用味觉体会季节的变迁,春天采蕨,摘水芹,夏天包粽子、剁辣椒,秋末冬初还会腌酸菜、做腐乳。我也知道如果在她床上看着一个用棉被包裹的物件,那一定是她在用老面发面,离吃到包子馒头也就不远了。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外婆走了,我也不能回家。我几乎无视了所有消息,放着弗兰克·辛纳屈的歌,闷头睡了一整天,醒来便开始翻木心的书,从来不熟悉也没看过木心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执念,觉得也许能从他的直言片语里,找到一些细微的共鸣。果然在《很好》里,翻到这么一段:
是啊,生命是什么啊?就是这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昨天中午,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妈妈电话里的第一句就是:「我想你奶奶了,她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啊转。」我两天两夜没睡的妈妈没有妈妈了。那一刻,我也只能宽慰她:「奶奶只是走了,她只是带走了那些她自己不愿意告诉我们的记忆,但是只要我们还记得她,她就一直还在。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法想去见她的时候就去见她,但是我们却能在想她的时候,自由自在地想她。直到我们都不在了,我们都走了,她才是真的走了。」
想起多年前看过的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里面有这么一段对话:
— 你生活得很简单,随着年岁的增大,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一天、一年,甚至一个世纪,对你来说没意味着什么?生死轮回?
— 动荡。我遇到某个人,知道了他的名字,说了几句话,然后他死了。其他人就像海浪,潮来潮去。又像麦浪,随风飘荡。
我想幸得我们会死,幸得我们是向死而生,人生中的所有相逢均在悲喜交集处。
你想,倘若你真的获得永生,所有的生命在你眼里不过是一夜花谢花开。面对沧海桑田,你永远无法找回当年走出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太长,长到必须用另一个生命来见证。或许,两百年前见过的一个不知名的陌生人再相遇,才能让你感知有朋友相知的可贵。倘若你活过了一万四千年,时间不过是一道风景,无数的风花雪月,无数的爱人都幻化如烟。你所见的人类知识在重复愚蠢的错误里慢慢前进,前进到你必须依靠人类进步中创造的所有只是才能挽留住自己的记忆。而无论你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探求,也不过是囿于时代的认知,而此刻这孤独的永生是否真的值得追求?
我想,外婆肯定比我更早想清楚了这一切,不言语只体验。或许早已预知自己人生路的她,最后静静的看着我,也不过是在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人生的终章,观察着身边的亲人来来往往。既然生命里时时刻刻都是不知如何是好,理既得,心随安,静看自己人生的这幕戏。
哥伦比亚的倒影的内容简介
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木心,被陈丹青(《退步集》作者)尊称为“吾师”的前辈,《南方周末》专版评论并由陈子善、陈村、何立伟等名家共荐的文学大师。木心是个“异数”,双重性质的“异数”。木心自身的气质、禀赋,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而偏偏落在最宿命地湮没个人才具的历史时期,本是注定了要枯萎夭折的,但他存在,而且成熟,沉默几十年,终于扬名海外。专题评论木心的文学活动,是后事,是大事,是盛事。他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感情与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优雅、从容、洗练、蕴藉,极为讲究。洋粹他也懂,国粹他也懂,但他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弄出个“三明治”来,就像他用水墨来描画他的风景,他是用纯粹的中文书写思维,来表述他对世界的体认与感怀。木心写过一则谈张爱玲的随感,因为没有点名,只写“她”,不大为人知。“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起首就石破天惊,木心对张爱玲的点评可谓一针见血。惊异于他的熨帖。他也用汉赋般的奇字,但不怪。他的文字有节奏,一读就发现标点的重要。他可以东一个棋西一个棋地走,到后来平平服服。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至于业余爱好写作的文友更知道得无边无际,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一不留神,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大师”太多了,时不时还要诺贝尔一下。真正热爱中文的朋友,读读木心吧,他们立刻矮下去瘪下去并好笑起来。我日前破例看电视,拍的是上海的作家。看的时候不由叹气,如果木心仍在上海,哪里轮得到我等说嘴?——陈村
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我看完电影和小说《时时刻刻》脑海中一蹦而出的感受。“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是从“时时刻刻”这一线索中追寻到这一句话,可是我想不起来原来这句话是木心说的。它出自木心的一篇散文《很好》,我并没有看过这篇只有几百字的散文,但高中那时候就知道了木心,知道了他那首《从前慢》,从来都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木心,就像我一直把那句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藏掖着矫情时拿出来是抒发情感的肤浅理解。
《时时刻刻》是我这个学期我看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电影只是个“附和品”,小说所呈现的内心比电影呈现的更多,这就是不同艺术形式带来的审美体验,电影注定给的更多的是画面感,小说不能说没有3画面感,我觉得小说的画面感始终是自己脑海中的“一平米”的天地。文字的呈现让人物更加的鲜明,电影不能大量的呈现小说的作者对人物的额外解释。
三个女性,三个不同的时代,三个人都因《达洛维夫人》这本书联系在了一起,她们都呈现出对生命的不安,生命似乎一尘不变似乎被抑制了。
伍尔夫是小说的作者,一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居住在伦敦郊区患有神经质的作家,对自由的渴望,感情丰富的她敏感,冲动,不安。对死有很深的认识,所以最后她奋不顾身的走进了流水缓急的河流里。
布朗太太是小说的读者,是二战末一个家庭主妇,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肚子里即将有一位孩子出世,她本是一位沉默只爱看书的女生,因为丹的出现以及求婚让他从一个从书中感知生活到真正的体会生活。她受不了当不好家庭主妇的自己,做不出一个完美的蛋糕,生活的一尘不变让他们对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感到慌张。布朗太太曾经在九点自杀未遂,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生下孩子就离家出走。
克拉莉莎的绰号叫“达洛维夫人”。一个九十年代居住在纽约的自己去买花并且要开一场PATY的编辑。她最好的朋友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好多年,她照顾了他好多年,一直都假装坚强的她在理查德的前男友出现时彻底的大哭起来。
三段故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克拉莉莎和理查德。三个女性之中我觉得我最像克拉莉莎。
我曾经觉得我能在任何一本我看过的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前的不说,就是最近,我觉得我是福楼拜笔下的追求不合时宜的爱情追求者包法利夫人,我觉得我像夏洛蒂笔下的独立自尊的简爱,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投入到这样的人生的愁思中,我又觉得我像哈代笔下的敢于追求但被命运捉弄的具有悲剧性的人物。
我找不到自己,但同时证明我一直都不停的在寻找着自己。我不想把主题引向正能量,我们的逃避可能是另一种比现在更有挑战性的东西。生命总要有矛盾,总要有挫折,我想起了大二的时候看的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时候不懂小说的政治主题,只是懵懵懂懂的体会到一丝的爱情,特蕾莎睡觉的时候紧紧的握住托马斯的手,有时候指甲会在托马斯的手掌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我依稀记得托马斯和特蕾莎冷战时,特蕾莎远离了家,可是对于彼此来说却是一个好的转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时候的直觉居然是一种日常想要抽离的状态,是一种默默地一声不吭地离开没有得到挽留。
我的读书笔记上有这样一句话“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的,期待嫁人的年轻女子期盼的是她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当时抄下这句话是因为她说中了我想做很多事情的原因,因为不了解,因为还没有经历过,因为好奇所以我想追求那些哪怕在外人看来是错误的事情。
弗洛伊德说 “女性是一块黑暗殖民地” ,没有人能真正的了解女性想要什么,连女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所以我说我像很多人也无可厚非了。
很多时刻,当我无所事事一天下来比累并值得的一天更加的疲惫,我的头会更加的痛,我想这就是一种“轻”,一种对生命安然的不好的感知。我讨厌自己的那一天一定是颓废无脑的。
所以,躁起来吧,总要做一些别的事情。